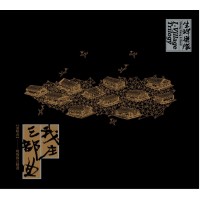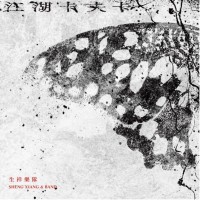菸草沒落,野蓮出庄。
2000年代中我在嘉義的海產攤初遇破布子炒水蓮、山蘇又蒸魚,記憶被撞開了裂縫。除了靜素躺在飯桌上與母親相對眼,沒想到對面烏尚可如此靈活!更納悶:我們不常吃的野蓮,何以出庄且易名?困惑中,我夾一顆對面烏入嘴,兒時的澀苦在舌根處轉甘甜,令我不禁揣想:難道離家夠久、吃苦夠多,才得品嚐對面烏?
那滋味引我再度回家。
我回返母親獨自採收、製作對面烏,以及每餐一碟的場景,試圖探究她的心境。我跟著她走出除草後的第一期稻田,腰夾的臉盆上擠滿挑好的野菜。她疲憊,但幾絲愜意流露。我領會水田的賞賜,不再排斥連吃一週斛菜或冇筒梗炒黃豆醬。七月半,我安靜看她備料,蒸芋頭粄,不再質疑家裡人愈少、粄卻愈厚,明瞭那是對外出子女的召喚與祝福。年三十下午,我忍住玩興,盯著屋後的大鋁鍋,乖乖掌火。母親在灶下忙進忙出,姊姊們已催緊手腳,仍不免招念。我面前這一鍋大封,不只是我對食物的至高期待,更是家族團聚的圓心,以及長媳的年終考評。我不能失手啊!必須把火餵好、餵穩。
社造牽線,去阿里山拜訪鄒族,主人留客午飯。村長端出我本以為客家地道的樹豆湯,食物地域觀隨被破解,提醒我穿越鄉愁之必要。我拜會本土種黃豆的復育者,探訪幾位回鄉開設豆腐坊的朋友。他們難忘豆腐郎吆喝,以及植物蛋白質之於社區的重要;他們倡議的保種運動,連接了母親掛曬在窗櫺上的各種蔬果種子。幾位原住民採集文化的研究者解開我的野菜邊界,放打烏子流浪。期間,美濃愛鄉協進會的朋友呼應創作計畫,廣泛訪談,證實了食物傳統的堅韌延續力。他們關注後菸草時代,農民尋找另類經濟作物的歷程,理解野蓮產業的在地意義,及其全球化機會與困境。
食物的部首是「女」--她們是食物的主要採集者、製作者、保存者與教育者。但面帕粄連繫父親:考試、繳菸得意,他帶去粄仔店;稿賞工人,叫我去包回來。凡此,面帕粄總造成米食最高級感。工作至嘉義,必吃火雞肉飯;看各家以自製雞油淋飯,亦予我同樣印象。
生祥讀詞,聯想日本的「B級美食」比賽,主角是非主流的鄉土菜肴。我們的食物場景若有配樂,亦當是在地流行音樂:流動攤車的叫賣聲與隨取音樂、婚宴場上的中西混種音樂,以及李文古笑科劇、金光布袋戲、神明生日晚會中的戲仿音樂等等,生祥總稱為「B級音樂」。
那麼,就請乘著B級音樂,聽我們唱這些食物與人的流浪故事。